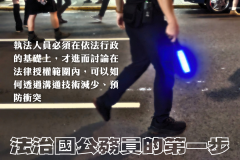文/台權會實習生 曾郁芯
今(2021)年8月,警方用束帶壓制抗爭者。警察為國家行政權的一部分,必須依法行政,若法制層面未有瑕疵,警方所作所為便不易被檢討,因此,所有問題須回到「集會遊行法」上做更深入地探討。
本次講座由台權會副秘書長王曦主持,邀請魏培軒(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及許仁碩(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助理教授)兩位老師共同分析台日抗爭現場之警察執法手段。
集會遊行之意義與重要性
魏培軒老師主要盤點以下三點做說明,分別為:
一、法規範的創造過程
認為民主與人權需透過法律共同實現,而法律需要一套透過民主程序且具有正當性之創造過程。
二、參與政治並非只是行使投票權
講者貼切舉例:「英國說法國不是民主國家,英國才是最老牌的民主國家。然而法國在大革命成功之後,盧梭則說英國只有在投票的時候才是自由的。投票結束之後,英國人又會變成國王的奴隸。」
三、正規與非正規的溝通管道
人民並非仰賴四年一次的投票決定所有國家未來決策。人民理應可以隨時發表意見,藉此凝結輿論進而施壓正規溝通管道裡的決策成員。
人權vs民主
接著魏培軒老師說明人權與民主相剋情形,自由主義者認為:「人權比較重要,民主對他們來說是保護個人利益的一種道具。」換言之,為了保護我們的基本權利,所以我們參與民主。而共和主義卻認為:「所謂自由,不僅僅是個人自由,而是活在特定社會之個人。如欠缺民主共識,並不是現代社會之個人自由。」後續德國當代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則認為:「人權是用來實現民主。除了還原人權價值,國家做任何決定皆須充分溝通,藉此創造權利,在法治社會中主張正當性。」如將人權與民主放置翹翹板上,始終難以達到平衡。
政治性權利=選舉投票+集會遊行
身處在資訊量爆炸的時代,是否真的要走上街頭集會遊行才能直接達到訴求?義大利哲學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曾說:「網路動員雖然方便,但仍是虛假動員。」深怕產生萬人響應,一人到場的窘境。魏培軒老師不諱言指出,實體集會遊行仍有其必要性,原因在於透過現實及物理集結,來傳播重要訊息給社會大眾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台灣集會遊行三部曲
而說到實體集會遊行,魏培軒老師解釋台灣集會遊行發展可分為三階段:
一、戒嚴時期對於集會結社自由之限制
對於集會結社是完全的控制且利用權力壓制言論,以當時戒嚴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有執行下列事項之權:
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
上述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必要時並得解散之。
二、解嚴後的政府控管方式
解嚴後取代戒嚴法,出現了人民團體法、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合稱國安三法)。尤其集會遊行法,明明是最直接影響民眾,在修法上卻總是修改幅度最小。此三法讓解嚴後台灣與戒嚴時並無二致,原因在於對當時政府而言,走上社運的人皆是流氓,仍須嚴格懲處。
三、大法官解釋中的集會遊行法
釋憲迫使行政院及立法院修改,卻延伸許多問題(如釋字445號解釋)。大法官冠冕堂皇地重新包裝集會遊行法,名義上國家為了保護大家,所以創造集會遊行法,但從立法緣由回溯卻發現集會遊行法最大的功能其實是限制集會遊行。
我國集會遊行法目前採行許可制,而許可制使得人民與政府的角色翻轉。換言之,人民能不能走上街頭發表言論,變成是政府可以進行審查,人民要獲得政府許可才可集會。而政府原本角色定位在於保護人民,卻演變成監督者角色去認為集會遊行者是潛在犯罪者。
許可制所產生的行政裁量,大法官解釋有兩套標準:
1.將言論區分為高價值與低價值的言論。
2.涉及內容與不涉及內容之其他事項。
換言之,人民可組織集會並發表言論,但地點、時間及用何種方式,政府機關可任意決定,演變成政府讓集會變成毫無意義的展演。
行政裁量權空間之最大化
魏培軒老師說明,政府給予警察機關過大的裁量範圍與權限。警察權限來自於警職法,其法條中何謂緊急狀況?何謂必要手段?模糊抽象的法律概念皆可能產生警察執法過當的風險,而且近年來警察機關常利用「妨害公務」之罪名冠上社運者,理由在於現今社會難以明確認定該集會遊行的負責人為何人,因此警察難以使用「集會遊行法」送辦,比起「集會遊行法」成立「妨害公務」條件舉證容易,程序也較為簡單。
接著由長期研究日本警察體制的許仁碩老師說明在日本是如何處理集會遊行。
日本警察體制
許仁碩講者解釋日本公安警察基礎知識,源自於戰前的「特別高等警察」之傳統思想(消滅的不是人命,是思想),處理對「國家犯罪」的部門、編制龐大情報部門與鎮暴部隊,亦在警察內部地位高於其他部門,且編制、預算上高度保密,最重要在於,實質不受縣市警察管轄,組織與預算採取中央一條鞭式。
接著許仁碩講者說明日本集會遊行三部曲
第一部曲:現場防處
活用鎮暴戰術,如「三明治」隊形(民眾可上街遊行,但警察隊伍環繞起來,所以示威民眾旁邊都是警察)、「隧道式」臨檢(只留幾個出入口)、「長蛇陣」交管(只能站半個人行道寬,目的在於不讓示威民眾聚集一起),且於集會遊行中,警方對現場參與者的刑事追訴,如「假摔公妨」(假摔妨害公務)、少年隊(造成學生心理壓力)、法庭程序攻防(法庭程序漫長),及便衣警察的運用,藉此打探情報、擾亂現場、盯住想要抓住的人。
第二部曲:事前疏導
預防性逮捕、搜索(日本法:凶器準備集合罪)及空間封鎖、場地借用、物理拒絕與集會遊行許可。
第三部曲:平時佈建
日常生活的「刑案化」,如民眾租屋、搬家、寄信,就認為是「偽造文書」,公民團體開戶、租屋就形成「詐欺」等,持續監控與蒐集情報,呈現「情蒐→偵查→情蒐」之循環,且利用社會性排除,結合管區員警的地毯式作戰與大學合作及公然情蒐跟監等騷擾行為。
日本給台灣教訓
乍看之下警察「依法行政」,背地卻擁有高度解釋空間,故「監察機制」扮演重要角色在於,能夠代表民主性、確保獨立性及反映民意,也充分人員編制,以便增加專業調查能力與技能、充足人力、適切單位配置,且擁有法律授權,能依法調查及懲處個案與通案改革之權限。
Q&A
1.日本警察跟蹤社運份子,只有針對負責人嗎?還是對全部社運分子皆是如此?
許仁碩講者表示,日本警察機關監控成本高,而日本在60、70年代社運興盛,投注大量公安警察,隨之社運逐漸減少下來,日本警方仍有許多資源,反之,台灣後期社運趨緩,政府立即解散保安警察,藉此可說明日本官僚形成後就自我目的化,自行找下一個目標,間接告訴政府,警察體制就是要金錢及權力等資源,而下任廳長仍是日本警方的人,這就是一個循環,有些法院判決會顯示,日本監視會消耗龐大的人力資源,亦說明日本警方需如此多人力來維持編制。
2.現在台灣用束帶壓制民眾,國外會使用嗎?台灣什麼時候開始使用束帶?
許仁碩講者認為,束帶的使用在於可大量逮捕及拘束,假設自己是警察,在面對抗爭分子,只有一付手銬的情況下,怎麼一口氣抓起來?且使用手銬鑰匙要配對,銬起來警方要負責,使用束帶就可以綁完就置之不理,那為什麼我們平時抓刑犯不用束帶?因為前提是對方不會掙脫,行使束帶之優點在於快速且大量逮捕拘束對方之人身自由,單靠手銬是不行的。
3.公安這個詞是否能和台灣調查局及憲兵對比?
許仁碩講者解釋,日本比較特別把公安設在警察內部,需要用特別法去限縮活動範圍,它的規範度很低,可動用全國警察資源,以台灣來說,台灣調查局要調動台灣警察是不容易的,所以日本將公安設在警察內部是很特殊,可動用行政機關的資源相較台灣高很多。
4.有些人認為使用束帶壓制人民無不好?兩位講者怎麼看待此想法?
許仁碩講者認為,這存在緊急避難的問題,而我們現在看的是警方系統性派發的常態使用,這是有問題的,並不是侵害強度高不高的問題,而是警方豈能自行選擇使用何種工具壓制人民?此舉動在集會遊行權上侵害非常大。
而魏培軒學者則表示,有些人認為警察用束帶是人道且進步的作為,事實上從集會遊行的經驗,過去不流行束帶,從野草莓學運的時候,皆未使用束帶,如果警察不相信抗爭者,那就依法使用合法的警械,「行使束帶」是警方公然違法的象徵。
結語:集會遊行權,需你我重視
魏培軒講者言之,先撇除政府是否侵害社運者,對政府而言蒐集社運者的情報是最基礎的,無論是尊重人權的國家,社運者個資將會有一定的掌握能力,但不見得是警察機關(如台灣情資單位),另外,警察使用警械需要遵守警械條例,束帶很明顯的不是警械,因為所謂的「警械」要有合理的規範及使用規格,如果只針對評估壓制人體侵害度為唯一考量依據,乍看之下無關痛癢,但未來必產生難以預測的風險。
完整影片可見此連結
➢|延伸閱讀
- 【投書】對警察「假摔」吹響改革哨音(許仁碩)
https://www.tahr.org.tw/news/2925 - 我們的集會遊行權遇到問題 台權會申請路權被駁回
https://www.tahr.org.tw/news/2491 - 【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政府是禁止恐怖份子還是阻止國際公民社會的交流?
https://www.tahr.org.tw/news/2467 - 【新聞稿】南鐵最後抗爭對峙 警方將函送屋主和學生代表(聯合新聞網,2021)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569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