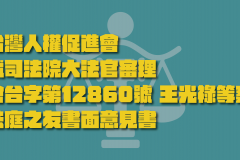【台灣人權促進會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祿等案 法庭之友書面意見書】
意見書撰寫者:
涂予尹 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施逸翔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一、台權會就本案爭點1.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部分「我國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上述權利之憲法依據、理論基礎、內涵及範圍為何?」說明回應如下:
我國憲法雖未明文肯認原住民(族)之「狩獵權」、「文化權」,抑或「(狩獵)文化權」,不過原住民(族)之是項權利,應可自憲法保障人性尊嚴之原則,乃至於「人格權」、「良心自由」等而推得。原因在於狩獵不但是若干原住民(族)重要的傳統生活方式之一,復與各該原住民(族)成員的群體身分成員攸關。不論個別原住民(族)成員於現今之生活中是否仍實際從事狩獵活動,狩獵及其所關聯的文化活動,均已深切影響各該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乃至於文化傳承,構成個別原住民(族)成員自我群體身分認同的重要成分,與其人格權、良心自由,乃至於人性尊嚴之實踐等高度相關。
鈞院於過去所作成之歷號解釋中,業已多次闡述「人格權」之重要性,以及憲法實踐「人性尊嚴」保障之意義等。其中有關「人格權」之部分,釋字第664號解釋理由書第2段明揭:「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22條保障。」。又如釋字第737號解釋理由書第7段提到:「羈押強制處分限制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將使其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隔離,非特予其生理、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其...人格權之影響亦甚重大,故應...慎重從事」等。
至於有關「人性尊嚴」部分, 鈞院向來之立場係認定,人民之自由權利雖非憲法基本權利清單所明文肯認,但其實踐具有人性尊嚴之重要性者,即有透過憲法第22條「其他自由或權利」之概括條款予以掌握之正當性,且與「人性尊嚴」之實踐或「人格權」之限制或侵害有關之法律,至少應受「較嚴格」審查基準之司法違憲審查。例如釋字第791號解釋理由書第26段即提到:「系爭規定...禁止有配偶者與第三人間發生性行為,係對個人得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之性行為自由,亦即性自主權,所為之限制。按性自主權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為個人自主決定權之一環,與人性尊嚴密切相關,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性自主權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是系爭規定一對性自主權之限制,是否合於比例原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又如釋字第748號解釋理由書第13段亦提到:「適婚人民而無配偶者,本有結婚自由,包含「是否結婚」暨「與何人結婚」之自由...。該項自主決定攸關人格健全發展與人性尊嚴之維護,為重要之基本權(a fundamental right),應受憲法第22條之保障。」;同號解釋理由書第15段則明揭,以事涉人性尊嚴實踐之性傾向,作為差別待遇之手段,則該項差別待遇之立法「應適用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以判斷其合憲性,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外,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並須具有實質關聯,始符合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另外,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該項規定性質上固屬「基本國策」,具「方針條款」之性質;但該項規定之存在同時象徵著我國憲法是以「民族國家構建」(nation-building)的模式,而非「族裔文化中立」的國家觀。加拿大籍學者Will Kymlicka的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相關理論,或可為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提供詮釋方向上的指引。Kymlicka提到:所謂「民族國家構建」,並非指政府只能提倡一種「社會性文化」(societal culture),而是應鼓勵在一個國家內並存兩個以上的社會性文化,正如同加拿大、瑞士、比利時或西班牙等標榜為多民族國家那般。具體的執行方式上,應「確保所有的少數民族群體均享有維持其獨特文化的機會,使得所有人民文化成員身分的優點均能被平等保障,而包括自治在內的特別權利,則是補償陷於系統性弱勢地位的少數群體成員的方法之一。也就是說,真正的平等並非全然一致的待遇,而是足以涵容不同需求的差別待遇。
據此,國內有學者認為在Kymlicka的觀點之下,多元民族國家必須正視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才能真正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以「公民身分」(citizenship)為基礎,賦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權利與利益,正是以人們的群體成員身分為據進行合理的差別待遇。亦即,在公民身分的基礎之上,自由國家的基本權利架構,應從「族裔文化中立」的立場,往「群體區別」的方向調整,肯認少數民族群體(national minorities)及少數族裔群體(ethnic groups)享有與多數或優勢群體不同的權利,前者將聚焦於若干「自決權利」(self-government rights),後者則是涵括各種「多元族裔權利」(polyethnic rights)。
綜上所述,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權,既然與「人格權」或「人性尊嚴」的實踐高度相關,其實證法上之基礎,至少能自憲法第22條之概括規定尋得。至於其權利主體,則應認為是個人基於其「群體身分」而能得主張。不具原住民身分之人民,即便狩獵對於其人格自我實現有正面作用,亦不能主張所謂(狩獵)文化權。相對的,文化上受到狩獵傳統或其活動之影響,且該項文化構成各該原住民(族)群體成員身分認同之所繫者,即有主張該等基本權利(包括自由權與平等權等面向)之正當性。
二、台權會就本案爭點1.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部分「其性質屬於個人權或群體權或二者兼具?」說明回應如下:
縱然2009年立法院所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依其第 2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僅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並非憲法位階之人權保障,但人權公約仍可作為大法官於憲法解釋時,適用或參考之依據。如同本會在第一部份的主張,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雖非憲法明文肯認之權利,但卻與「人格權」或「人性尊嚴」的實踐高度相關。因此,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應可屬於公約位階三層次論中的第二個層次,亦即「非我國憲法已明文規定的公約權利,且具有相當於憲法權利之重要性者,得承認為非明文憲法權利。」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應屬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少數族群的權利。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1994年第23號一般性意見中,雖然開宗名義在第1段就指出,這一條賦予少數族群中的個人的權利,但卻又在第6.2段進一步指出雖然第27條所保障的是族群裡個人的權利,但正因為這個個人「仰賴於少數族群團體維持其文化、語言和宗教的能力。因此可能有也有必要由國家採取積極的措施以保障少數族群團體的身份認同以及其成員與團體內的其他成員享受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及一起信奉宗教的權利。」而這裡的文化權指的是什麼呢?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七段就明確指出「文化本身以多種形式表現,包括與土地資源的使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方式,原住民族的情況更是這樣。這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傳統活動和受到法律保障的住在保留區內的權利。」而國家有義務保護這項權利的目的,「是要確保有關少數族群的文化、宗教和社會特性得以存活和持續發展,從而加強整個社會的結構」。因此,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在性質上兼具個人權和群體權。
國際人權法專家曼弗雷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也在其著作《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評註》中解釋公約第27條的權利屬於少數族群中的個人,以及第27條中的集體因素,並引述道奧地利人權活動家菲里科斯·厄馬克拉(Felix Ermacora)關於公約第27條的主張「從個人的角度和從集體的角度對該條進行解釋都是可以的」、「第27條可以被理解為一條”群體保護規定”並且委員會也是以這一方式解釋該條的」,因此締約國有責任採取積極措施確保國內少數族群的存續。
又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多個涉及原住民族權利案件的個人申訴來文案例,幾乎都是根據公約第27條做成決定,包括拉夫雷斯訴加拿大案(Lovelace v. Canada)、盧比康湖營居部落訴加拿大案(Lubicon Lake Band v. Canada)、基托克訴瑞典案(Kitok v. Sweden)、馬惠卡訴紐西蘭案(Mahuika v. New Zealand)都是。尤其是盧比康湖營居部落一案,雖然申訴人是以公約第1條自決權這項集體權來主張加拿大政府允許亞伯達省(Alberta)政府為了私人公司開發石油和探勘的利益,強制徵用盧比康湖營居印第安原住民族的領地,嚴重破壞他們的環境與經濟基礎,但人權事務委員會最終是以公約第27條受理這項申訴來文,最終並做成加拿大政府如果繼續以開發行為來威脅盧比康湖營居區的話,就構成違反公約第27條。
又《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雖沒有施行法確立其國內法律之效力,但中華民國政府在尚未退出聯合國之前,就已於1970年完成批准程序,又根據我國憲法第141條「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之規定,故我國也受到該公約之拘束而有國家義務落實該公約人權保障之規定。再根據該公約1997年所通過之有關原住民族權利的第23號一般性建議第4段,締約國應「承認並尊重獨特的原住民族文化、歷史、語言和生活方式」、「確保原住民族成員的自由及在尊嚴和權利方面平等,不受任何歧視」、「向原住民族提供條件,使其能夠以符合自己文化特性的方式獲得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確保原住民族能夠行使自己的權利,保留和發揚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習俗。」而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作為「以符合自己文化特性的方式獲得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屬於上述各項締約國應保障的原住民族權利,自無可疑。
最後,參考日本法院在二風谷案的判決書,本案法官是日本少數引用國際人權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並結合日本憲法第13條作成判斷、依此證明日本阿依努族為原住民族,並因此確認日本阿依努族應享有隨之而來的文化(享有)權的法官。本案判決書的幾個關鍵段落,以一次三段論來確認這樣的主張:「不屬於多數構成員的少數民族文化,其本質在於不與多數民族同化而維持其民族性。而享有民族固有文化的權利,亦為人格的生存所必要之重要權利。依憲法第13條,屬於少數民族的阿依努民族享有其固有文化之權利,應受保障……(憲法第13條的目的在於)表明個人主義、民主主義之原理。亦即在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中,以個人為終極價值;國家於其國政態度上,承認作為構成員的國民每個人的人格價值……阿依努民族為保有其文化獨特性之民族,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其文化享有權受到保護;而我國亦應依據憲法第98條第2項之規定,負有誠實遵守義務……。」吳豪人教授在專書《野蠻的復權》中引用學者手島武雄主張「原住民族權利的保障,只是把國際人權法典現存的諸原則,平等適用於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的原住民族而已。」
綜上所述,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在性質上應兼具個人權利與群體權。
三、台權會就本案爭點「2.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環境生態保護,尤其與野生動物保育之平衡(1)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主張如何與憲法所規定之環境與生態保護要求相平衡?」說明回應如下: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固然有「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的規定,惟相較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的主張,源自於憲法有關人性尊嚴、人格權等之保障,「環境與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的價值僅屬方針條款,在規範的性質與實踐優先順序上應有所不同。
除非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環境與生態保護兼籌並顧」條款在特定個案中,能夠確立特定的基本權主體,且其基本權主張與實踐人性尊嚴的關聯性上強於狩獵文化權的主張,始可能得到「環境與生態要求」優先於(狩獵)文化權的結論。
四、台權會就本案爭點「2.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環境生態保護,尤其與野生動物保育之平衡(2)野生動物保育是否屬於憲法位階的保護法益?其憲法依據、理論基礎、內涵及範圍為何?(3)國家對於原住民(族)之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得為如何之管制,始屬合憲?(4)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規定,就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係採事前許可制,是否合憲?除上開條文所定之「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之目的外,是否應包括自用之目的(94年2月5日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參照)?」說明回應如下:
倘若涉及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因與特定原住民(族)群體成員憲法上所保障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價值等有關,至少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基準,理由如前所述。
在採取「較嚴格審查基準」的前提上,政府就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採「事前許可制」,其所追求者必須是重要的管制利益,且採取事前許可制與該等重要管制利益之間,必須具有實質關聯性,方能得到合憲結論。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規範目的,應在於物種多樣性等自然資源的保育(參照該法第1條之規定)。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的規定,自然資源之保育應具有相當程度之重要性,殆無可疑。
然而,「保育」不等於一率禁止「殺戮」,只要不構成「竭澤而漁」、傷害野生動物「生生不息」的可能性,基於人類所追求的生存等利益,應有一定的取用野生動物資源的空間。
暫時將原住民(族)是否僅能「基於傳統文化、祭儀」之目的獵捕野生動物之問題置之不論。獵捕行為固然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之計畫性,但在更多時候,獵捕決策涉及許多事前未必能事前周延計畫之因素。一律採取「事前許可制」規範原住民之獵捕行為,甚至未必有助於「維護物種多樣性等自然資源保育」等管制目的之達成。亦即,「事前許可制」與「自然資源保育」目的之間,是否具有實質關聯性,要非無疑。
野生動物保育法之執行,首要問題應在於如何判斷對於野生動物資源的取用,是否傷害其「生生不息」的可能性?必須特別指出的是:該法係主流(多數)種族或族裔群體所掌控的國會所通過,其所反映者乃主流(多數)種族或族裔群體觀點或利益的投射。然而,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倘若與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相重疊,理應尊重原住民(族)的觀點與智慧,由原住民(族)自主決定如何權衡生活、經濟利益與野生動物保育的利益,而非由主流(多數)種族或族裔群體觀點的主管機關從事事前許可,方能呼應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有關尊重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的誡命。
同理,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將阻卻獵捕野生動物不法要件限定於「基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亦有過度剝奪原住民(族)自主、自決權利(力)之嫌。畢竟,何種情形得以阻卻獵捕野生動物之不法要件,與其由中央主管機關決之,毋寧交由原住民(族)以自治方式加以認定,方符合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多元文化之旨趣。由原住民(族)之自治單位,立於原住民(族)生活、生存必要性之視角,判斷系爭獵捕野生動物之行為,是否有傷害野生動物「生生不息」可能性之虞,方符合管制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實質關聯性的要求。
五、台權會就本案爭點3、自製獵槍部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就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魚槍,免除刑罰,而僅處以行政罰。上開規定將得免除刑罰之狩獵工具限於自製獵槍、魚槍,是否違憲?又上開免除刑罰之規定未及於(自製)空氣槍,是否違憲?」說明回應如下:
現行規定的問題在於:免除刑罰限定在「狩獵」工具必須為「自製」獵槍、魚槍,這使得主張適用免刑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必須證明其獵捕野生動物所持有的獵槍或魚槍為自製。然而,槍械的製作有一定的難度,為了該項免除刑罰規定適用明確的目的,勢必會發展出僅有特定「規格」的獵槍或魚槍,方為犯罪嫌疑人得以據以主張免除刑罰的獵槍或魚槍,而且這些「規格」也勢必相對落後。畢竟,能夠透過「自製」方式生產的獵槍或魚槍,相較於能夠透過機械大量生產、製造的獵槍、魚槍,其作用效率等勢必有所不如。然而,不具原住民(族)身分者,有權透過新科技經營其現代生活,何以具原住民(族)身分者,就必須抱殘守缺,只能以相對落後的「自製」獵槍、魚槍繼續狩獵?
何況,「自製」獵槍、魚槍有其危險性。在原住民透過狩獵等方式經營其生活、追求其價值的同時,國家卻透過法律,課予其行使與人性尊嚴相繫的權利時,須承受自製並使用獵槍、魚槍可能導致自身身體甚至生命遭到危害的負擔,此種法律規定與其執行,不啻為主流(多數)群體對於弱勢(少數)群體的壓迫或宰制。
徵諸 鈞院釋字第748號解釋,以及本項意見書前揭說明,法律等公權力行為涉及主流/多數群體與弱勢/少數種族或族裔群體間差別待遇者,關於其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之司法審查,亦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基準,亦即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外,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並須具有實質關聯,始符合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範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參照該條例第1條規定)。該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得依法申請自製獵槍、魚槍,作為免除刑罰之前提,其目的應在於尊重原住民異於非原住民之生活方式,徵諸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國家應對原住民之「教育文化」、「經濟土地」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之規定,該條例在免除刑罰要件之設計上採取「原住民/ 非原住民」之差別待遇,所追求之公共利益應具有相當程度之重要性。惟該條例第21條規定,原住民(族)群體成員免除該條例相關刑罰之要件,須以使用經許可之「自製」獵槍、魚槍為前提,則有「包含不足」之嫌疑;畢竟,倘若規範目的在於尊重原住民之文化及其自然資源利用之方式,即不應否認原住民(族)運用現代化方式利用自然資源、並追尋其文化實踐之權利。是以,前述規定限制原住民(族)僅能利用經許可之「自製」獵槍、魚槍從事獵捕,方可能免刑之規定,與該條所欲追求之尊重原住民族文化、自然資源利用方式等公共利益之間,欠缺實質關聯,應已構成違憲。